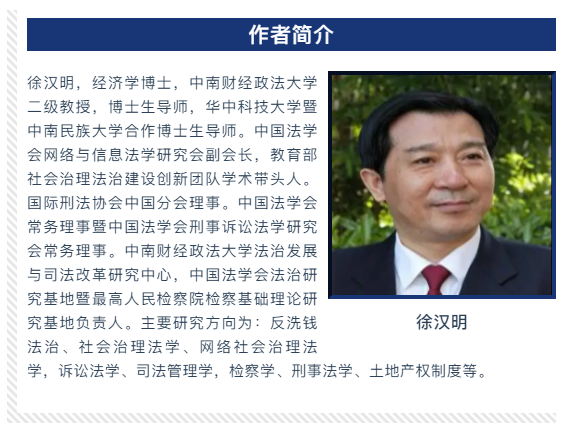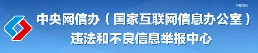謝謝敬波副校長,謝謝梅夏英院長!
我是作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地方受邀的代表,有幸出席外貿大涉外法治研究院成立大會暨首屆涉外法治高端論壇。
涉外法治研究院的成立是我國高等院校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標志性成果。她意味著以外貿大法律人與法學教育工作者為代表的第一方陣,吹響了中國高校率先進軍“統籌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高地的集結號;意味著我國法學教育模式的轉型跨越,由“國際法學”被“10+X”包含與萎縮模式向地位提升、并駕齊驅、協調統一新型模式跨越;亦意味著適應新時代法學教育“三大體系”構建并從國際法學“三大體系”薄弱環節切入,為當代中國在國際治理格局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提供大批卓越涉外法治人才,爭奪發展制高點開辟了新路徑!
我們為之鼓與呼!
我是大法官江必新教授,著名國際法學黃進資深教授,著名民法學、21世紀民法典奠基人利明一級資深教授,知名國際經濟法學沈世寶資深教授的忠實粉絲。現就學習踐行“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談點初步體會,求教于在座的著名專家,與大家交流。
一、堅持以“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為引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世界的眼光、戰略家的睿智、政治家的胸懷、大國領袖擔當的氣魄,在領導億萬人民開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偉大征程的關鍵期,對全球人類社會發展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精準判斷,創造性地提出了統籌“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兩個大局的系列新理念新論斷新思想新戰略。梳理總結其涵蓋六個層面,即——
統籌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兩個大局層面。提出了“堅決維護以聯合國為基石的世界秩序論”“積極參與國際立法論”“積極參與國際執法論”“積極參加國際司法機構和司法活動論”“做好涉外與國際法律服務論”“加強國際法治人才隊伍建設論”“積極開展法律外交論”。
推進全球治理格局、治理體制、治理規則層面。提出了“三個前所未有論”,即:“我們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臺中央”“前所未有的更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所未有的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國際形勢波譎云詭的風險挑戰論”“中國快速崛起必定面臨限制、牽制論”,即:面臨既有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的限制,又面臨美國等西方守成大國的牽制;“參與全球治理的目的論”“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負責任大國義不容辭的責任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力和話語權論”;“給國際治理格局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爭奪發展制高點論”;“爭取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新安排中體現和尊重中國應有地位和作用論”。
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層面。提出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論”“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論”“用統一適用的規則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未來論”“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民主化,共同推進國際關系合理化論”。
構建利益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層面。提出“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和平、發展、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論”“推進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論”“推進合作多元的開放體系建設論”“健全對外開放建設保障體系論”“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論”“維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論”“支持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20國集團等平臺機制化建設論”“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論”。
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層面。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論”“居安思危的憂患論”“防范風險的先手棋、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論”;“五個不讓論”,即:“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構建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預警預防體系論”。
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層面。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論”;“堅持立德樹人、德育為先導向論”“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發展涉外法律業務論”“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論”。
這一整套新范疇新命題新論斷構成了內容豐富、體系完整、邏輯嚴密,具有成熟哲學方法和鮮明時代面向的國際法治理論體系,堪稱“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
其產生、發展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直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期”的國際波譎云詭形勢判斷與牢牢把握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是“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產生發展的客觀基礎。消解統籌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能力不完全適應的矛盾是“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產生發展的社會根源。破解國際執法、司法、涉外法律服務卓越法治人才供給不充分的難題,是催生“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的現實條件。新中國70年國際法治從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貢獻;到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再到新時代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重跨越轉型,是“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發展完善的時代需求。
這一理論特征具有實踐性、科學性和時代性。其實踐性根植于當代中國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統籌協調實踐,是70年參與全球治理的經驗結晶。其科學性在于詮釋了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中國模式、道路、制度,詮釋了統籌兩個大局,辦好兩件大事質的規定性,是21世紀偉大馬克思主義國際法治觀的科學表達。其時代性集中體現在,為推進全球治理體制、治理規則變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打造共商共建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整體性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爭奪更多制度性權利和話語權提供了“中國方案”。
認真研究、宣傳、踐行“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對于構建涉外法治“三大體系”,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提升涉外法治服務能力,擴大中國法的域外適用空間,發揮涉外法治在參與全球治理格局、治理體制、治理規則變革,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基礎性、戰略性、先導性作用意義重大而深遠。
二、直面國際法治人才建設短板
用“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檢視,雖然,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為涉外法治領域輸送了大批涉外法治人才。但是,這同統籌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兩個大局,辦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的戰略要求比,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存在突出短板。具體而言:
1.整體數量的短板。“二戰”后,全球人類社會發展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人民政權的建立。第一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率領億萬人民奮力突破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封鎖與武裝顛覆、干涉、侵略,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加入了WTO與國際互聯網組織。這使中國在站起來、富起來的過程中獲得了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貨物、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的規則運用權,逐步參加了國際規則制定、執法、司法活動的領域。
隨著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呈現“東升西降”的突出特征,其核心變量和主要推動力是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推進和不可逆轉。“兩個大局,一張卷子”,不僅給國內法治提出了急迫要求,更暴露出國際法治人才在涉外立法、涉外執法、涉外司法,涉外法學研究中捉襟見肘的短板。正如著名法學家黃進教授指出的,“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存在總量偏小、質量不高、經驗不足等問題”。
例如,我國在國際競爭中仍然尚缺乏強大的國際規則話語權,尤其是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法院等國際立法、司法、仲裁、法律服務等國際組織中任職的人員偏少,并且任職人員中處于領導層、發揮領袖作用的不多。據有關資料統計,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的雇員僅占1.46%,不僅遠遠低于美國的6.75%,而且排名在菲律賓、印度、俄羅斯之后,屬于40個“任職人數不足”的國家之列,這與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
2.人才質量短板。法治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依托,涉外法治人才是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競爭的重要力量。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交匯期,涉外法治人才參與國際政治、經濟、貿易、網絡、執法、司法中暴露出整體性水平不高,在同以美國守成大國逆全球化、逆國際規則適用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應對“長臂管轄”,中國法的國際適用能力等方面整體不足,常常呈現“有理說不出、說了不管用”的尷尬。
如何打破以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戰略上圍堵、遏制和打壓,規則博弈上“規鎖”,思想理論文化上“污名化”、西化和“分化”?
從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整體現狀看,存在“六有六缺”現象,即:有學科缺頂層設計、有學術缺思想、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有專業缺謀略、有法務缺影響。尤其是在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長期以來拘泥于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智識知識傳授,忽視伊斯蘭語系國家、斯拉夫語系國家、南亞語系國家法律制度的傳授,由此帶來這些領域法治人才的奇缺,有的只能以外語人才濫竽充數,致使在國際貨物、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活動中常常吃虧上當。
3.培養體系短板。這主要表現在:學術體系方面。以AI技術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催生人類社會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態領域規則的多樣化與適用的便捷化,型塑了以守成大國為主導、新型市場體國家整體性興起相互博弈,催生了國際組織規則體系與適用體系的轉型變化,給21世紀國際法治“三大體系”提出革新的要求。如國際網絡法治、氣候法治等缺失,海洋法實施主權國家沖突平衡,對以美國為主導局部戰爭的國際法庭審判程序完善等,伊斯蘭語系等“一帶一路”國家的法律查明,等等。所有這些都給國際法理論的科學發展提出了種種挑戰。
教學體系方面。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的教學體系未能與國家戰略充分對接,以《普通高校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法學類)》來看,高校在法學專業核心課程設置方面遵循的“10+X”分類設置模式,將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劃入“X”范疇,從原來的必修課變為限定選修課,僅保留“國際法”。這就弱化了國際法學知識訓練,深刻影響學生的國際視野和知識結構,嚴重制約涉外法治大局建設。
培養模式方面,我國高校未能依據各自區域優勢與辦學特點進行差異化的涉外人才法治培養,并且推行以問題為導向的法律實踐型教學,教育“同質化”現象嚴重。實踐應用方面,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的教學培養仍然側重于以法條解讀和學理闡釋為主的課堂講授方式,模擬法庭、法律診所、模擬談判、境外法律實習等教學方式未能實現有效普及。同時,高校和政府、實務部門之間的壁壘機制仍須進一步打通,尤其是政府涉外部門、涉外企業、涉外律所和具備師資條件的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亟待加強。
三、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路徑
1.構建國際法治“三大體系”建設。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把“習近平國際法治理論”貫穿國際法學一流學科建設的全過程,堅持把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擺在同等重要位置,全面提升國際法治學科在法治體系中的地位。
建一流的國際法學院,將國際法學升格為法學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創造條件在各高校開設國際法學本科專業,擴大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碩士、博士學位授權點招生規模,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在“六類人才”(黨政、企業管理、專業技術、高技能人、農村實用、社會工作)隊伍中的比重。
同時,對標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格局、治理體系、治理規則變革,及“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優化國際法學課程體系;根據聯合國、國際組織、地區組織、“一帶一路”國家法治建設進程,可增設聯合國法、國際網絡法、歐盟法、國際數字經濟法、國際數字貨幣法、亞太國家國別法、“一帶一路”國家國別法等,以適應國際法治體系和法治能力現代化新需求。探索國際法學課程體系與法學“10+X”課程體系相對應相匹配的運行模式,形成國內法治“三大體系”與國際法治“三大體系”相平行的大格局體系。
要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人類社會以四大聯合國為基礎平臺在構建世界格局、全球治理體系實踐創設的治理規則進行創新性轉化,豐富發展21世紀國際法治“三大體系”,具體可探索“聯合國法+國際經濟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環境防治法+國際私法+國際司法(公證、仲裁、法院)+歐盟法+一帶一路國別法+英美法系國別法+大陸法系國別法+國際組織規約+聯合國通用六種語言(英語、漢語、法語、俄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小語種國家語言)+經貿學、社會學、文化學、生態學”的課程體系。為新時代涉外人才傳授工商共建共治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規則、程序與成果與失敗的典型樣態,全面提升學生參與全球治理事務的統籌兩個大局、辦好兩件大事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提供“國際法學+語言、經貿、社會、文化”等學習機會,深化實化細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
2.強化國際法律實踐教育。高校須注重與國際組織、仲裁機構、知名律所、跨國公司等合作,充實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師資力量,實現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高質量培育與引導;建立健全高校與涉外的政府部門、司法機關、企業、法律服務機構等之間聯合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的協同工作機制,重點是將法院、仲裁、司法、商務系統等涉外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更有效地引入法律院校,強化和創新實踐教學。同時,針對具體涉外法律事務和問題,發展完善“法律診所”“境外實習”“模擬法庭”等培養方式,并通過技術賦能實現實時、實地的“線上討論”“云小組學習”,不斷拓展學生深度參與涉外法律實踐的途徑與方式。
3.創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模式。以培養“復合型、創新型、能力型”卓越涉外法治人才為目標,推動國內高校與國際組織、知名大學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協同創新,整合法治資源,提高國際法治開放度;建立“國際法學+”雙專業雙學位培養機制,強化涉外法律課程的雙語教學與英語教學;探索“國內+海外”中外合作培養機制,拓寬與世界上高水平大學合作交流渠道。
4.深化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體制機制改革。設立中央依法治國委員會涉外法治人才建設辦公室,統籌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人才培養的目標規劃、頂層設計、政策支持、行動進程、保障措施、組織領導,評估督導等中長期發展規劃。
要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規模、質量、效果引入高校“雙一流”建設評價體系。所有涉外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及科研機構,都要與高校建立涉外法治人才需求聯合培養、定向培養、短期培訓、國別法制咨信服務、重大課題攻關等合作機制,拓寬涉外法治人才生長渠道,以彌補“一帶一路”與“走出去”戰略實施中涉外法治人才供給不足的短板。
擴大涉外律師、公證、仲裁等法律服務機構的設立,所有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和經濟發達對外開放度高的市(縣),都要創造條件建立涉外法律服務所(站)。到2035年前,我國涉外律師、公證、仲裁法律服務人員規模應達到100萬,并與國內法律服務規模形成1:3的科學結構。
建立涉外法治人才評價考核模式,把重視涉外法治人才工作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納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考核評價的范圍。凡有涉外工作的地方都必須把黨政領導是否重視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選拔與使用作為單獨的指標進行考核評價,在相同條件下,對涉外法治工作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有實績見成效的干部優先提拔使用。要把加快“一流國際法學院”建設納入地方“十四五”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加大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經費投入,加強涉外法治專門教師隊伍建設,推進涉外法治信息化。